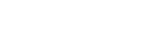21世纪的Labubu与17世纪的荷兰郁金香:人性、投机和泡沫的四百年轮回
“听说,世间所有的泡沫都如同无脚鸟,只能不断飞翔,一旦落地,便是消亡之时。”
01 历史镜鉴:欲望的种子
1593年,第一株郁金香球茎从奥斯曼帝国漂洋过海,抵达荷兰莱顿。起初,它只是贵族花园里供人观赏的奢侈品。到了1608年,一颗郁金香球茎的价值竟能换取价值3万法郎的珠宝,其珍贵程度可见一斑。
1634年开始,全民狂热席卷荷兰。扫烟囱的工人不惜抵押自己的工具,旧衣店的老妇也变卖了房产,只为能在郁金香市场中分得一杯羹,憧憬着一片花瓣带来的美好未来。1637年,“永远的奥古斯都”郁金香标价高达6700荷兰盾,这笔钱足以在阿姆斯特丹运河边买下一座豪宅,而当时普通人的年收入仅有150盾。
时光流转至2024年,设计师龙家升笔下的“九齿獠牙”精灵Labubu,以盲盒的形式登陆泡泡玛特。原价99元的玩偶,在二手市场被炒到了3188元。
2025年,一只限量薄荷色Labubu在拍卖会上更是以108万元的天价成交。Z世代的年轻人为了抢购Labubu,凌晨就开始排队,队伍从东京涩谷一直延伸到芝加哥密歇根大道。蕾哈娜还将Labubu挂在爱马仕包链上,社交媒体上#Labubu话题的播放量更是突破了亿次大关。
有人总结,这两者看似相隔四百年,商业逻辑却存在着跨时空的奇妙共振:
稀缺性制造
郁金香因病毒导致的条纹变异,被资本包装成一场“美学革命”;而Labubu的锯齿獠牙,则被重构为“亚文化图腾”,成为年轻人追捧的对象。
契约创新
荷兰酒馆里流通的球茎期货票据,与当代“拆盒未拆袋”的盲盒交易协议,本质上都是将不确定性转化为标准化的金融产品,让投机者有了可操作的空间。
杠杆率对比
1636年,荷兰农民抵押土地参与郁金香投机的比例高达47%;而到了2025年,在潮玩黄牛群体中,有32%的人使用消费贷加杠杆囤货,试图在市场中大赚一笔。
“所有的商业奇迹,往往都始于对稀缺性的想象,而泡沫的本质,则是人性对概率的集体性误判。”不过,二者也有明显差异。郁金香的稀缺性源于自然规律,而Labubu的稀缺性则是商业模式精心设计的结果。
02 人性的群体癫狂
1634年荷兰行会的记录显示,在郁金香交易会的参与者中,仅有12%是专业花商,其余皆是面包师、裁缝等跨界投机者。2024年对Labubu购买者的画像分析也表明,59%的购买者是从未接触过收藏品的Z世代。这充分印证了凯恩斯“动物精神”理论的永恒性,即当边际购买者从专业群体扩散至普罗大众时,市场便踏入了非理性繁荣的临界点。
荷兰法庭在1637年判决称“郁金香合约属赌博,不受法律保护”,这一判决导致3000份合同瞬间沦为废纸,无数投机者血本无归。而在当下的中国潮玩市场,46%的消费投诉都涉及“隐藏款概率不透明”,这暴露出新兴市场监管滞后于金融化创新的结构性矛盾。这种制度真空地带,恰恰成了投机资本最活跃的舞台。
Labubu的投机行为高度依赖互联网时代的传播与交易技术。盲盒机制激发了人们的“赌徒心理”,黄牛利用算法抢购进一步加剧了供需失衡,社交媒体则在其中推波助澜。现代投机者们坚信,“下一个接盘侠总会存在”。
03 泡沫破裂的代价:教训与警示
郁金香泡沫的崩溃,直接导致了荷兰经济的衰退。1637年崩盘后,3000人因债务违约破产,政府被迫宣布郁金香合约无效,荷兰的国际地位也被英国取代。更深层次的影响是价值观的冲击,喀尔文教派重新倡导节俭,讽刺画《愚人的花车》成为了贪婪的象征,时刻提醒着人们贪婪的后果。
Labubu目前尚未经历完整的经济周期,但风险已经逐渐显现。2025年,市场上仿品泛滥,如Lafufu等,导致市场秩序混乱,部分联名款价格暴跌40%;线下抢购冲突也时有发生。其发展轨迹与1990年代Beanie Babies泡沫破裂(价格暴跌96%)极为相似,Labubu的高估值已经脱离了基本面支撑。
不过,泡沫并非全然是坏事。郁金香狂热推动了荷兰花卉种植技术的革新,现代荷兰仍占据全球郁金香出口量的60%。Labubu则成就了泡泡玛特的全球化扩张,2024年其海外收入增长375%,带动中国潮玩产业规模突破140亿美元。关键在于,我们要在创新与风险之间找到平衡。郁金香泡沫的教训告诉我们,脱离实体价值的投机终将崩塌;而Labubu的启示则是,要警惕“情绪资产”的金融化异化。
四百年间,泡沫的载体从植物球茎变成了塑料玩偶,但人性对稀缺的追逐、对暴利的渴望从未改变。正如经济学家凯恩斯所说:“市场保持非理性的时间可能长于你保持偿付能力的时间。”无论是17世纪的荷兰,还是21世纪的全球市场,唯有回归价值本质、强化制度约束,才能在商业奇迹与投机狂潮之间找到可持续的平衡点。真正的商业文明,永远建立在对规律的敬畏之上。
“爱情是有时间性的,认识得太早或太晚都不行。泡沫也是如此——1637年荷兰人不懂,2025年我们假装不懂。”
(迪哥看财经,财经作家,前财经媒体人,基金与资产管理行业研究者,职业投资人,代表作《基金经理》、《资本剑客》、《基金经理之诚信的背后》、《股市风云三十年》等。)
马俊生的创业之路:从证券老兵到个人系公募掌舵者
假设金本位制复辟,国际金价还会有十倍涨幅?
银行系公募基金困局:当“规模虚胖”遇上权益跛脚
暂时没有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