吴晓波:如果梁启超盯着我们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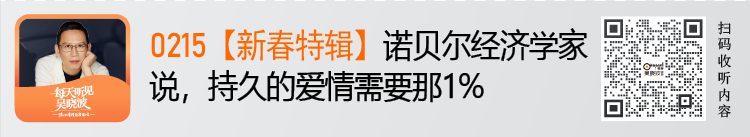
 “许知远笔下的梁启超既是历史的,也是当代的,是‘我们的梁启超’和‘梁启超的我们’。” 文 / 吴晓波(微信公众号:吴晓波频道)
“许知远笔下的梁启超既是历史的,也是当代的,是‘我们的梁启超’和‘梁启超的我们’。” 文 / 吴晓波(微信公众号:吴晓波频道)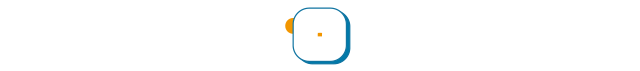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都是读书人,很早的时候便知道,无论在人世间怎么浪荡,最后一锤定音的,还是那本书。
跟我不同,你找写书的选题像一个赌徒,总指望着一把就梭哈。很多年前,有一位华人圈的商业巨子请你写传记,那是一个极珍贵的机会,我很是咽了几下口水。创作过半,某一次,巨子拿过一张纸和一支笔,写下十来个名字,然后推到你面前,细声说:“这些人,你就不要采访了。”你愁眉苦脸地说这事的时候,我笑得花枝乱颤。
后来某一年,在单向街的圆明园店,你对我说,打算写《新青年》。围绕那本杂志的人物和文章,勾勒五四一代的集体面貌。你很兴奋地说了几年,后来就没有下文了。
直到2015年,那年你快四十了吧,定下心来,决意写梁启超。2019年出版第一卷《青年变革者:梁启超1873—1898》,去年8月,出版第二卷《亡命:梁启超1898—1903》。

这个书要写五卷,估计得干上十年。这应该是能够留下来的作品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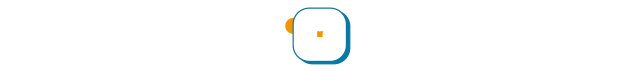
梁启超其实很难写的。
斯人一世雄笔,倚马可待,平生写下1400万文字。去世之后,丁文江、翁文灏等人编撰他的年谱长编,细节已到某昼某夕。
他又是一代通才和精力旺盛的社会活动家,行走国政、外交、经史、教育、财经诸界,触角达四方,交际遍天下,在三十年间,发动和参与了诸多关乎国运的重大事件,连“中华民族”一词,也是梁氏首倡。
所以,传主的强悍和事迹繁复,对作者会构成巨大的压迫。写梁启超,极其容易被他牵着鼻子走,疲于奔命,终而匍匐在地。
从你已完成的两卷来看,似乎跳出了这样的担忧。在《青年变革者》中尚有拘谨的部分,到了《亡命》已日渐从容,我相信以后的诸卷更值得期待。你写青年梁启超,是一个中国青年对另一个中国青年的直视,我分明读得出字里行间的同情与同理心,作者基本上完成了对传主在心理上的畏惧和精神上的克服。
为了写作此书,你去了梁启超流亡日本时的诸多故地,还赴夏威夷的火奴鲁鲁寻访。记得有一次闲聊,谈及在那里遇到孙文家的一位老太太,神态言辞,仍见民国风姿。
一个活泼泼的梁启超即将在许氏文本之中重生一回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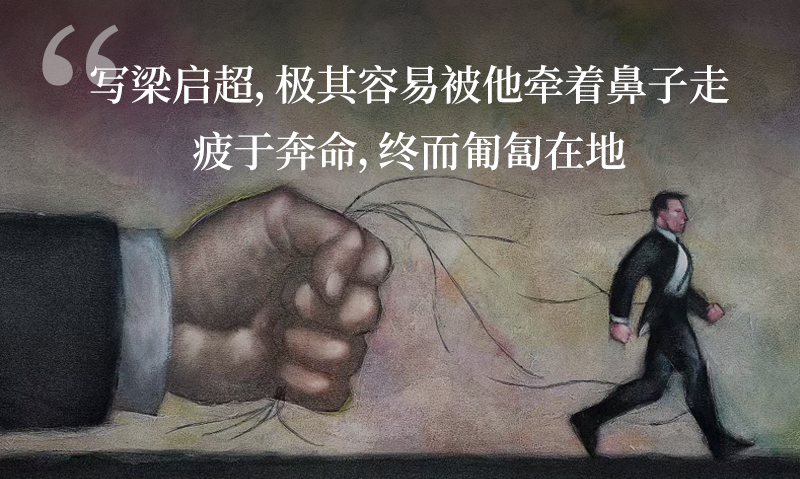
不过,随着传主阅历的日渐复杂,你一定会在历史线索、人事关系安排、学术能力、观念梳理乃至情绪上遭遇种种的挑战,它们是险峰、深渊和漩涡,无一可以轻易征服。
总而言之,梁启超不会饶过你,你将遍体鳞伤,惨胜而归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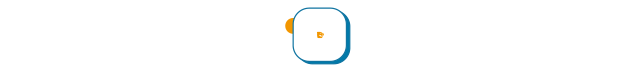
我读你写梁启超,有几种很别样的体验,这是读其他书从来没过的。在这里跟你唠唠,也是写这封信的原因。
作者许知远,传主梁启超,两个人我都挺熟的。你是二十多年的损友,被写者的平生也不陌生,我治近代企业史的时候,曾专题做过梁启超的内容,很多人不知道,他曾担任过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和盐务总署督办。
有趣的是,你们俩的缘分还挺深。你读的北大,梁启超是京师大学堂的章程起草人。你们还都少年成名,你大学毕业后不久,便在《经济观察报》担纲头版主笔。梁启超22岁随康有为“鼓动各省,公车上书”,成了变法的急先锋,26岁在上海创办《时务报》,主持笔政。28岁写《李鸿章传》,臧否当代人物。
你说梁启超很可能是中国最伟大的新闻记者,“我们迄今生活在他缔造的传统中”。我深以为然。
你们相差97岁,却都在青年时因各自的风云际会,站在了启蒙传播的中心,而那个时代也正是国家急速变革的大浪潮期。两人的写作风格乃至个性也颇有相似处,“万事纯任主观,自信力极强”,好写“大矣哉”的大块文章,很多观点和文字漏洞不少却星光熠熠、才华横溢。
所以,读你写青年梁启超,却恍惚看到两个不同世代的中国青年在并排奔跑,能听到你们的呼吸声和急促的喘息。你们都曾经被时代裹挟着往前急速冲刺,百年岁月,际遇迥异,但是同样有着浩荡与焦灼的底色。

有几次,读到一些细节,我会哈哈大笑。比如梁启超曾撰文提议弄一本《英文汉读法》,“凡读此书,不数月即可翻译英文书籍”,王宠惠大惊失色前去请教,两问三问后,梁启超知道自己唐突了,大惭,日后遂再也不提此事。我笑着想,梁公子换作许公子,估计也干得出这种事的。
还有一种阅读的体验,则是写作者的臭毛病,便是读着读着就会不由自主地想,如果我来写这一段会怎么写。写作的秘诀就在布局的疏密张合和对情节控制的轻重缓急,写作者各有奥妙和手段。
譬如,1900年,新世纪开张之际,梁启超在茫茫太平洋上写下《少年中国说》,如果我来写,应会独立成章,以此为焦点,前后铺陈,浓笔渲染。而你却将之列为一节中的一部分,并未突出处理。你应该有你的含蓄和考量,我据此把玩,趣味盎然,“此意非我无人传,此理舍君谁可言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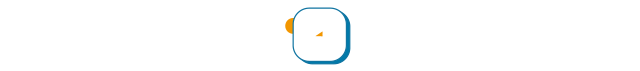
还有一种始终挥之不去的体验,是时时冒出来的错乱感。
梁启超的孙子梁从诫曾说,“我们梁门三代都是失败者”。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自我叙述,也是我读《梁启超传》时,常常回荡起的感叹。
已完成的两卷,时间中止于1903年,革命尚在酝酿,重建还未开始,而梁启超的人生也仅三十而立,他对中国乃至自己生命的看法,还将发生多次的转变。他的一生,遭遇通缉、暗杀、背叛与反背叛、同门操戈,甚至在国民舆情中,由少年英雄“堕落”到落伍遗老,如此种种的惊险和跌宕,都非我们这个世代所能想象。




不同年龄下的梁启超
但是,我同时又想,虽然已是百年前的人物,梁启超当年所面临的很多命题,到今天何尝已经全数解答,甚至在某些方面,是不是还在不断的反复与彷徨。我们对这个人物的热情,显然不仅仅是一次旁观式的考古或阅读,而是在那些惊心动魄的细节中,投影和冲击于内心,生发出关于自我命运和这个国家的痛苦追问。
知远你还记得吗,2004年——天哪,居然二十年前了,我为你的一本小书写过篇序言,题目是《总有一代人会实现我们的梦想》。如果梁先生给我们写个信,闹不好也会出这么一个标题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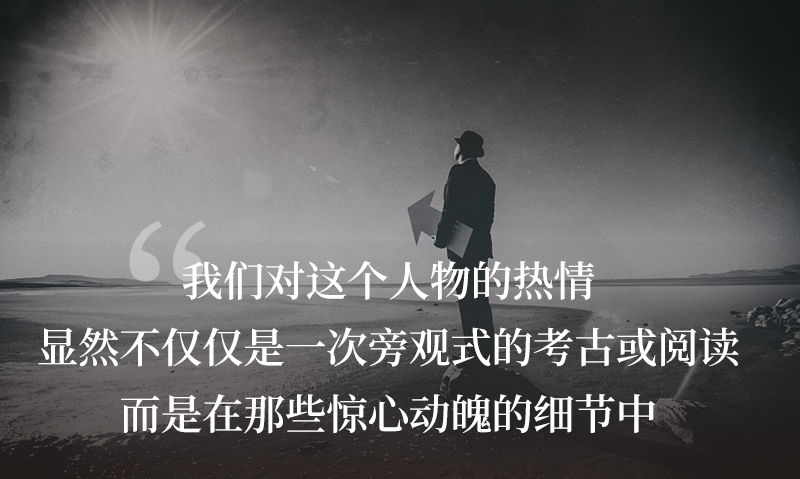
但是,二十年前的那份自信还在吗?
如果梁先生盯着我们问,我们接得住吗?
以及,在未来,我们的孩子们接得住吗?
因此,你笔下的梁启超既是历史的,也是当代的,是“我们的梁启超”和“梁启超的我们”。我们跟他在一起,有可能涅槃重生,也可能玉石俱焚。
最后说句闲话。
梁启超因“错取一肾”,殒于1929年的56岁。按你那个拖沓浪荡的脾气,接下来的三卷如果每隔三四年才交出一本,那么,全书完成之时,1976年生人的你恐怕正是梁启超去世时的年龄。
这种生命的“追赶”与“逼近”,也是我对此后诸卷的一个另类好奇。
你的《十三邀》很好,不过,能留下来的恐怕还是这卷书。
新年加油,知远同志。
 本篇作者 | 吴晓波 | 责任编辑 | 何梦飞主编 | 何梦飞 | 图源 | VCG 当新的春天来临时,“吴晓波季度讲堂”将和大家再次见面。2月29日至3月2日,“吴晓波季度讲堂”春季课《中国经济3000年》即将在西安开课,从中国经济3000年中,寻找未来的答案。点击下图▼立即报名
本篇作者 | 吴晓波 | 责任编辑 | 何梦飞主编 | 何梦飞 | 图源 | VCG 当新的春天来临时,“吴晓波季度讲堂”将和大家再次见面。2月29日至3月2日,“吴晓波季度讲堂”春季课《中国经济3000年》即将在西安开课,从中国经济3000年中,寻找未来的答案。点击下图▼立即报名


暂时没有评论




